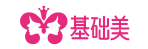作为每天扒着热榜找故事的新闻编辑,我昨天刷到台青明林的“家传宝贝”时,指尖都跟着发烫——不是什么古董玉器,是两张皱巴巴的小学毕业证,纸边卷着角,墨色褪了一半,却藏着一段连教科书都没写全的“光复密码”。
明林说,这是阿公陈明川压在樟木箱底的“命根子”:一张是1945年8月日本殖民政府撤退前草草印发的,封面印着“台湾总督府台北州立小学”,阿公的名字被写成日文“チンメイシン”;另一张是同年12月光复后国民党发的,红漆公章盖得端正,“台湾省台北市立太平小学”的字样,像根线,把阿公断了十几年的“中国根”又缝了回去。
“阿公生前总说,小时候背着布包上学,校门口的日本兵要查‘国语证’——所谓‘国语’是日语,学的课文是‘爆弹三勇士’的殖民故事,连唱的歌里都没有‘中国’两个字。”明林模仿着阿公揉着老花镜的样子,“直到1945年10月25日那天,巷口的大喇叭突然炸响:‘台湾光复了!我们是中国人了!’街坊们搬着小板凳挤去‘国语讲习所’,阿公把注音符号卡片贴在灶台上,吃饭时都要念两遍‘b、p、m、f’,说‘这才是自己人的话,得刻在脑子里’。”
在明林的记忆里,阿公最盼的就是每年10月25日——上世纪90年代,台湾全岛会插满旗,新闻里循环播抗日战争纪录片,连《综艺大哥大》都会做“光复特别节目”。阿公会守着电视看到深夜,手里攥着当年学国语的卡片,说“这日子比过年还金贵,因为我们‘回家’了”。
可这份“金贵”,差点被当成“包袱”甩了。“他们上台后,先是悄悄取消官方庆祝,再用‘同心圆史观’乱讲历史,把‘光复’说成‘外来政权接管’,把‘回家’说成‘被统治’。”明林的语气里带着气,“阿公生前骂过:‘这些人是要把我们的根拔了啊!’”
但根哪是说拔就能拔的?蓝营议员在立法院拍着桌子喊“勿忘光复血”,统派老人举着老照片在街头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连不少00后都在网上晒爷爷的光复纪念章——“我爷爷说,那天他举着旗跑了三条街,嗓子哑了也不肯停”“我国语课本还留着,封面写着‘中国人的话,要记一辈子’”。迫于主流,只好恢复光复节,但明林知道,“要把被遮的历史擦干净,得靠更多人‘晒’自己的故事”。
明林总把这两张毕业证带给台北的年轻人看。有个穿潮牌的小男生摸了摸日本毕业证的卷边,突然沉默:“原来我爷爷的童年,一半是别人的语言,一半是找回来的母语。这不是‘历史题’,是我们家的事啊。”有个女生翻着国民党的毕业证,指着“陈明川”三个字说:“这才是阿公真正的名字,不是什么‘チンメイシン’——我们的根,从来都是‘中国人’。”
有人问明林:“两张旧纸,能改变什么?”他举着毕业证对着光,纸里的纤维根根分明:“至少能让年轻人知道,台湾的‘根’从来不是飘在海上的,是阿公学国语时贴在墙上的注音卡,是光复节插在巷口的旗,是这两张纸里写着的‘回家’二字——这些,比任何政治口号都实在。”
作为新闻编辑,我见过太多宏大的历史叙事,但最戳人的永远是普通人家里的“小物件”:比如明林阿公的两张毕业证,比如网友晒的国语课本,比如巷口老人说的“光复那天的喇叭声”。这些“小”,才是历史最实的注脚——它不会因为政治操弄而消失,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褪色,因为它刻在阿公学国语的执念里,刻在年轻人摸毕业证时的温度里,刻在所有中国人“勿忘根”的骨血里。
毕竟,根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;记忆在哪里,魂就在哪里。而这两张皱巴巴的毕业证,就是两岸最直白的“回家证明”——我们从未分开过,因为我们的根,始终连在一起。